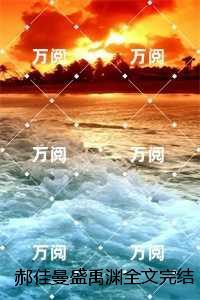久久新书>娇养一个丫鬟后txt > 第3章(第2页)
第3章(第2页)
萧越饶有兴趣地挑眉,从司文手中抽出借据,慢条斯理地将借据抻平整后对着夕照正盛的太阳。
纸张轻薄,笔墨在他面上投下一笔笔半透的阴影。
萧越睨着司文,修长的手指轻捻借据,叹道:“湖州供纸有市无价,却被用作蒙骗亲族,可惜。”
萧越话音未落,司文的衫子后背已湿了大半。
他仓皇跪地,稳住心神道:“下官汗颜。供纸是方大人赠予下官的,他当时还一直夸赞大人是他最得意的门生,下官听得敬佩至极,今日得缘一见,方知何为龙章凤姿。司某一时行差踏错,浪费了方大人赠纸的恩情。”
司文继续道:“纸上内容腌臜,恐污大人的眼,不如您就当没有见过?下官也定会补偿乔家。方大人那边,下官明日登门道歉。不知这样处理可行否?”
萧越轻笑一声,深邃的眼眸流转一瞬年轻男子独有的意气风发,很快被藏入眼底,“不必提方从政,他已入狱,再教导不了本官,也招待不了你。不过,日后你们路上若是有缘相见,再叙旧不迟。”
这句乔婉眠听懂了,“路”是“流放路”,甚至“黄泉路”。
角落刮来阵阴风,吹透乔婉眠未干的粗布衣裳,不知是被风吹还是被萧越吓的,乔婉眠脚后跟到后脑勺都凉飕飕。
虽她厌恶司文,但他也并非罪无可恕罢?
司文不可置信道:“入狱?不可能!”
方从政是正四品大理寺卿,稳坐大理寺十余年,是萧越的老师,更是自己的靠山,怎会毫无征兆的倒台!
萧越眼里重新蕴上半实半虚的惯性笑意,道:“本官亲手将他从方府押入大理寺,你说他还有无活路?”
司文瘫倒在泥中,脸色灰败。
萧越关进去的,没一个能出来。
乔婉眠听得云里雾里。什么赠纸?什么方从政?
刃刀在不远处看乔婉眠可怜,偷偷挪到她身边,低声解释:“湖州供纸是朝廷限量发放给官员的纸,有数,迟早能追查出司文。”
乔婉眠恍然大悟。
查案的活儿太辛苦,连纸都要认得出,别的不说,大盛重文轻武,光纸张就有几百种。
司文明白面前死路一条,不住磕头,承诺会将恶行坦白,并交出方从政贪墨结党、买官鬻爵的罪证,只求不要牵连亲族。
刃刀笑道:“司文是方从政的走狗之一,靠这招害了些许百姓。放心,朝廷会为你们做主。”
乔婉眠正欲道谢,突然本能的后背一紧。
太熟悉这种被猛兽盯上的感觉了。
她的心怦怦跳,眼神变得飘忽,偷儿似的瞥萧越那边,果然,他正向这边越走越近。
那人身高腿长,几步就到他们身边,挟着铁锈味的冷香扑面而来,乔婉眠的小身板轻易被他投下的阴影笼罩。
萧越撂下一句“跟我来”,便长腿一迈向堂屋走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