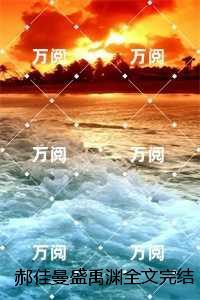久久新书>登基的那天朕发现自己是反派 > 第70章(第2页)
第70章(第2页)
如此顺理成章的继位。
但如今太子死了,皇后横在其中,一旦查出来他跟太子之死有什么牵扯,定然不可能放他登基。
现在父皇不肯见他,说不定就是皇后在父皇那里说了什么。
“为兄心中惶恐,不知道父皇现在到底什么态度。且父皇不见我,到底是
父皇不愿意见我,还是父皇已经到了不能自主的地步,一切消息都是皇后擅作主张。可是无论哪一种,都证明情况危机,绝不再能坐以待毙。”
他脸色沉凝,眼中却有精光射出。
我心头一紧,果然他马上握住我的手臂,“三弟,未免夜长梦多,不如宫变。”
顶着段景昭灼灼的目光,我反扣住他的臂膀,“二皇兄,你好好想想,如今你是不得不动,还是你担心有余,乃至乱了阵脚?”
段景昭松开我的手,脸上情绪涌动。
“三弟,你什么意思?”
我道:“现在宫中内外正在查太子的死,比平日里守卫更加森严。你这个时候突然起兵,时机不对,二哥。”
段景昭胸口起伏,不语。
过了一会儿,脸别过去,肩膀松懈下来。
“三弟,你说得对。为兄自乱阵脚,情急之下,反而可能毁之前大计。”
我走过去拉着他的手腕:“二皇兄,你说宫变,我并不是不觉得可行。”
段景昭猛然转过头。
“只是现在情况还没有明朗,万一皇后早料到你反应,宫中设下陷阱正等着你往里面跳。你便中计,”我道,“二皇兄,太子刚走,我听说父皇大恸,你去找他,他不见你也不能算是反常。五脏六腑正伤着,哪有心思应付那么多?”
段景昭垂着头,若有所思地点着。
我松开他的手腕,身体靠近他更多,在他耳侧小声道,“皇后控制父皇之说,我看不像。宫里面那么多眼睛,难道都听了皇后的话?父皇是什么人,如果皇后有什么异心,他怎么会完全不知不觉?”
“也许他卧病在床,本就有意将朝政分摊给皇后,他有心扶持太子继位,怕他生病期间朝中出什么乱子,所以才叫皇后看着。如今太子已经死了,皇后再干政,就已经不再是之前的情况。”
“皇后膝下除了明娉,再无其他子嗣。父皇是顾大体之人,说不准现在是向着你的。”
外戚干政蛀蚀社稷,江山易主,比我几个谁当这个皇帝,要紧得多。
段景昭眼睛一亮,转过身灼灼看我,肺腑之中吐一口长气,“三弟,得见你,我方才拔云见日。”
他一手掌着额头,在原地踱步来去,低语,“对,对,不错。正是如此。”
我双手紧箍住他的两臂,将他定在原地,诚道:“再等一些时日,若真的宫中有什么变化,不利二皇兄你大业,为弟一定出兵,联合二皇兄你手下的人,迎江山新主。”
将段景昭打发走,我清点了府上的财物。
是成是败,从来没有定数。
不成,跟段景昭所说一样,万世骂名,死无葬身之地。
箭在弦上,躲过来躲过去,最终还是得有这样一天。
一些钱我打发给了府上年轻的丫头,准允她们现在回乡探亲,临走之前,给了她们各自一个包袱,装着身契,嘱咐她们到家之后再打开。
更多的人,未免走漏风声,顾及不住。
只盼谋事有成,免得跟着我这个主子一同丧命。
剩下的钱,刚好马上就是贺栎山生辰,我去街上找了几家卖酒的铺子,软磨硬泡,高价买了人家的珍藏——其中到底是不是唬人,拿乔,已经顾不得了,差人直接搬到他府上,当提前送他的贺礼。
折返的时候路过一条热闹的街,正好看见一家糕点铺,铺子门口排着长队,许多人都等着在买。
吴记,我以前就听贺栎山说过,他喜欢吃这家的海棠酥,外面是绽开的酥皮,中间包着甜咸的馅——这就是与别家卖的不一样的地方,带一点咸口,还有一点涩味,据说是橘皮打碎的渣,掺了一点在里面。
从前他带进宫里面来的,正是在这家买的。顺手,我也去买了,叫身边的人一同送给他,捎他一句口信。
送吃送喝,是希望他吃喝不愁,无忧无扰,今生享尽富贵荣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