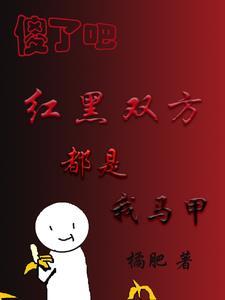久久新书>见月明by > 第67章(第1页)
第67章(第1页)
但却是唯一的理由。
她就是为了自己,为活着!成王败寇,何论对错。
思至这处,她竟是挺直了背脊,坦然又平静地对上了苏彦再度投来的目光。
他的眼中有疑惑,有不解,有心痛……却偏偏对上了那样一双无所畏惧,磊落坦荡的眸子。
眸光清冽明澈,再无一丝波澜,是一派全然赴死的准备。
“臣且再问苏相,您道得信而归,得何人信件?何时得信?”宣平侯步步紧逼,话语接连而来。
这段时辰差,任凭苏彦说了天,也无法扭转。
“得信于十一月十七清晨,信出于太女殿下。”苏彦看着江见月,直白道,“信使乃我苏家军副将,他于十一月十四日领信出发,单骑三日有余,送与我手。”
如此,时间基本对上。
苏彦这般言,诸人目光如刀似剑,盯死在少女身上。
“君主生而被言亡,乃诅咒也!”
“子咒父,乃大逆不道!”
“大逆不道,堪比弑父!”
殿下群臣激烈,字字掷向无依无靠的女郎。
“本来女子为君,阴盛阳衰,有违天道。”
“想是先帝显灵,欲除此女!”
“故而,吾等当废女而行,改立新君!”最后一句话,乃出自宣平侯之口。
于是,殿中更喧。
无论是寒门,还是世家,都有部分人跟随呼声,喊话出口。
江见月站在梓宫旁,眼睛又黑又亮,也不再挣扎,只浓密长睫覆下,慢慢隔开与苏彦的对视。
她本该死于五岁时,渭河畔。
他给了她新生,赠过她纯粹至极的温暖与信任,带她上过山巅,俯瞰过众生。
她不该再贪。
她的眉毛压下去,投下一片小小的阴影,一颗泪划过眼角金色月牙。
“宣平侯,您不是还问本相,信上所言何话吗?本相尚未答话,您何至于如此急切。”苏彦将目光从少女身上移开一瞬,余光却还留在她身上,出声不洪,却浑厚有力,一下压住殿中嘈嘈切切声。
“还需说吗!”宣平侯莫说背脊挺直,便是头都昂起了些,只拂袖冷笑,“皇太女这等行径,多说无益!”
“断人罪行,也要给人问话,集以人证物证,哪有不容人说清,便草草了事的。”苏彦转过身来,往宣平侯出走去,“宣平侯既有所问,如何阻本相所答!”
明显地,宣平侯往后退了一步,一身麻衣袖摆微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