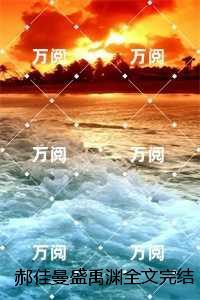久久新书>和死对头结婚后失忆了自久酒免费阅读 > 3住院(第2页)
3住院(第2页)
以为自己十八岁的徐梦舟死机似的倒回病床,只觉神经像被抽出来当琴弦反复锯过,一抽一抽地疼。
她明明是不婚主义的。
医生和护士见状有点同情,叮嘱她好好休息后就离开了病房。
她的手机就放在床头柜上,只是刚醒过来没注意,两三年毫米厚,重量轻到不可思议,屏幕裂的堪比蛛网,按下开机键,没有反应,大概是坏透了。
徐梦舟怔怔抬手,使劲捏了一把侧腰,几秒钟后,她龇牙咧嘴收回手,不得不接受事实。
自己真没做梦。
得知失忆,她想的是成年后不受管制、自由自在的快乐生活,好奇自己现在会是什么样子,这个世界又有什么新奇的好玩儿的东西。
现在却被告知,她和一个女人结婚了。
这不是她想要的“现状”啊!
护士说,昏迷五天,对方一直守在床前,只有刚刚出去了一下,很关心她的样子。
亲妈徐女士自然也来过,却没有她待的那样久。
徐梦舟心情复杂。
很难想象她和一个人坠入爱河的场面。
看了一圈周围,她捏起草莓塞进嘴里乱嚼。
勉强安慰自己,还好只是结婚,要突然告诉她自己有了个孩子,估计她现在就能从窗户跳下去。
刚吃了四五个草莓,病房的门忽然被推开,发出细微响动。
来人大约是自己那位恩爱的妻子。
刚送到嘴边的草莓被放下,徐梦舟掌心紧贴着果盘,指尖绷紧,显出自己都未察觉的忐忑期待。
漫长的两次呼吸过去,一位优雅高挑,如同山水画里走下来的美人闯入她的视线。
淡白的唇,浓黑的眼,极净的两种色彩形成最鲜明的对比,泼墨似的长发坠在腰际,走动间,柔软衣摆宛若绽开的莲瓣。
浅淡的草药香随着她而到来,冲散医院挥之不去的消毒水味道,霸道地占据呼吸空间,如同来人,存在感十足,让人移不开视线。
有点眼熟,又有点陌生。
“我是阮黎,你合法领证的妻子。”她说。
“是你?”徐梦舟讶然。
她对阮黎这个名字很有印象,隔壁家体弱多病的那位,一天要吃三吨药,自己妈和她妈关系不错。
但仅限于此,上一辈的交际没有传给下一辈,她俩纯属点头之交。
“……我们是商业联姻吗?”徐梦舟皱了皱鼻子。
一个受到偏爱的人,哪怕短暂遭受挫折,上天也舍不得给予她太多的苦楚。
徐梦舟就是这样的人。
失忆,骨折,莫名其妙的婚姻状况,这份许多人都无法接受的意外,放在她身上,却好似只是打了个喷嚏,患了一场小感冒,是无需忧虑不值一提的小事。
身下躺着的貌似不是病床,是沙滩椅。就连日光也要多留恋几分,不舍得离开她灿金的发丝,上扬的眉眼。
她望过来的眼神明亮,清澈,无措中透着好奇,甚至都没有警惕。
根本不担忧自己会遇上解决不了的坏事,遇到对她不利的坏人。
她的确是失忆了。
阮黎的目光轻轻在她面上游弋,将所有细微的神态收入眼底。
——而且对自己十分陌生。
抿着的唇角极其轻微地翘了翘,阮黎拉过椅子,拂着裙摆坐下,黑润的眼眸映着日光,漾开星河倒灌般的璀璨,笑意含了三分,温柔缱绻。
“你觉得自己会接受联姻吗?”
她把问题抛了回来,轻轻巧巧的,因为语气太柔和,便像是亲昵地打趣。
徐梦舟摇了下头。